洞察号的 “鼹鼠”探测器暂停在火星表面 “挖坑”
NASA的洞察号火星着陆器于2月12日在火星表面设置热量探测器,该探测器正式的名称是“热流和物理特性探测仪”(HP3)。 版权:NASA/JPL-Caltech/DLR NASA 的洞察号火星着陆器(Mars InSight lander)拥有一个特别的探测器,可以钻入到火星表面以下16英尺(5米)的深度,并对火星内部的热量进行测量。在2月28日周四那天,一根16英寸(40厘米)长的探测器将自己捶入了火星的表土里,它是洞察号热流和物理特性探测仪(Heat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Package,HP3)的一部分,但在它从外壳中伸出四分之三的长度后,就停止继续钻入火星地表;3月2日进行了第二次锤击之后,也不再有任何动静。数据显示,这根被称为“鼹鼠”(mole)的探测器正处于15度角的倾斜状态。 [rml_read_more] 科学家怀疑“鼹鼠”撞到了一块岩石或是砾石。由于洞察号周围的火星地表并没有什么石块,所以研究团队一开始认为着陆探测器所在的地表下方石块也会相对较少。即便如此,科学家还是对“鼹鼠”做过特别的设计,让它能将小石块推开,或者绕开石块蜿蜒向下。“鼹鼠”由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German Aerospace Center,DLR)为洞察号设计提供,在洞察号发射之前,已经反复对它进行过这样的测试。 “研究团队决定暂时停止‘鼹鼠’的锤击,以便更细致周详地分析现在的情况,制定出应对这一难题的策略。” HP3 的首席研究员、来自DLR的蒂尔曼•施波恩(Tilman Spohn)在一篇博文中这样写道,他还提到研究团队希望在进一步锤击之前暂缓两周的时间。 数据显示,“鼹鼠”探测器自身仍在按照预期继续工作:在加热到18华氏度(约零下7.8摄氏度)之后,它对这一热量在火星土壤中的消散速度进行了测量。这种热量消散的特性被称为导热性(thermal conductivity), “鼹鼠”背后有一条用来拴住它的系绳,而导热性则有助于校准嵌在这条系绳里的传感器。一旦“鼹鼠”足够深入火星土壤,系绳中的传感器就能测量来自火星内部的行星热量,一种由放射性物质衰变以及火星最初形成时残留的能量所产生的自然热量。 研究团队在3月5日~3月10日进行进一步的加热测试,以测量火星表土的导热性。研究人员还将利用洞察号面板上的辐射计测量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化。火星的卫星火卫一(Phobos)将于本周多次在火星和太阳之间掠过,就像一朵云遮住阳光,造成的火星日食会让洞察号周围的火星表面变暗变冷。 火星埃律西昂平原上的日落,由洞察号拍摄于第101个火星日。 版权:NASA/JPL-Caltech/DLR 参考: [1]https://www.nasa.gov/feature/jpl/mars-insight-landers-mole-pauses-digging [2]https://www.dlr.de/blogs/en/desktopdefault.aspx/tabid-5893/9577_read-1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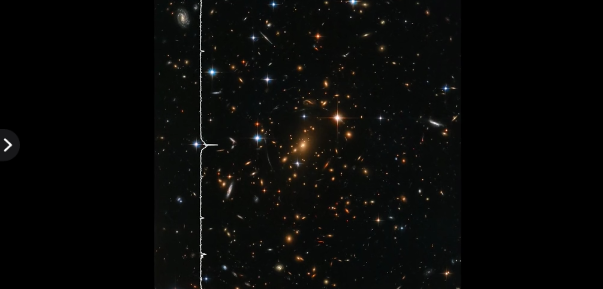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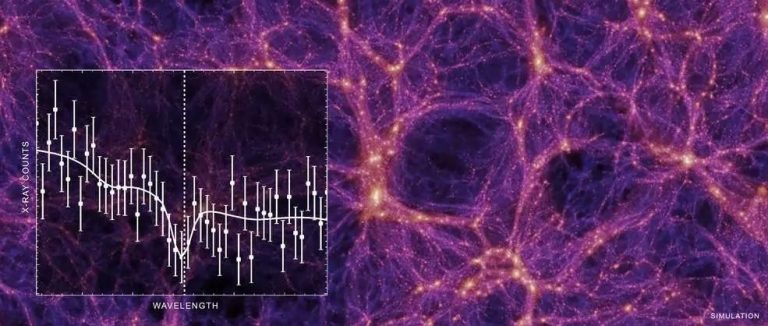



 还有个事情
还有个事情